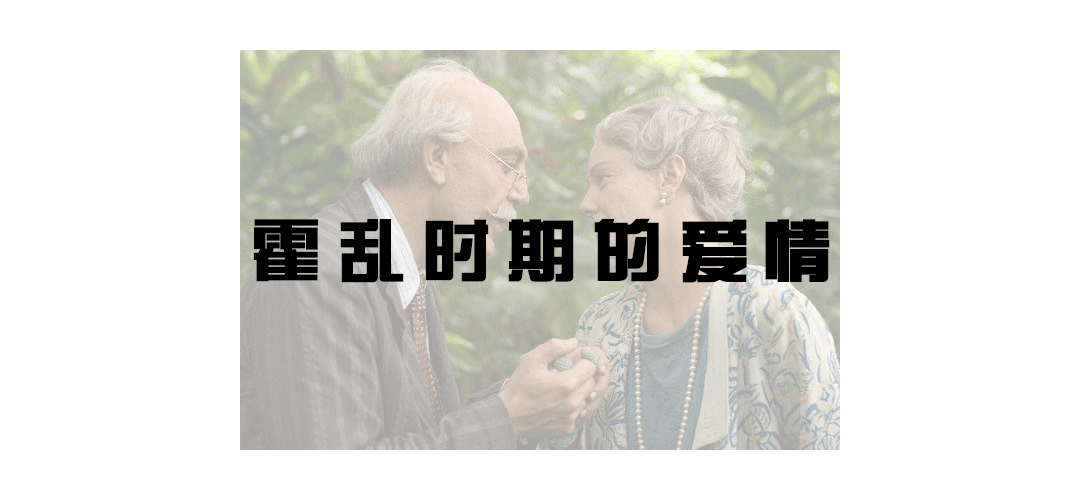
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
她不会流一滴眼泪, 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乐见寡妇做的事情。
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
两人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此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面非一个难以间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僧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那个被诗歌的魔力理想化了的姑娘原本的模样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将她从昔日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她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 在他悄悄地望着她却不让她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她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与洛达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她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但他的出神最终让他丧失了这种愉悦的机会:神秘的宗教音乐对他当时的灵魂来说是那么不痛不痒,于是他试着用爱的华尔兹为它注人激情,最后,洛达里奥.图古特不得不把他从唱诗班中开除了。
但一个星期日,她突然发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她一个人拉的。他原本不是她会选择的那种人,但他那过时的眼镜、神甫似的长袍,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神秘感激起了她难以抵抗的好奇心,而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
弱者永远无法进人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 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
她回过头,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作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龙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低硬的双唇。他离她那么近,就像在子时弥撒躁动的人群中看到他的那次一样。 但与那时不同,此刻她没有感到爱情的震撼,而是坠人了失望的深渊。
在那一瞬间, 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她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 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她只想出了一句话:“我的上帝啊!这个可怜的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冲她笑了笑,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想跟她一起走,但她挥了挥手,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一
“不,请别这样。”她对他说,“忘了吧。”
那天下午,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他孤身一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
这份迟来的顿悟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